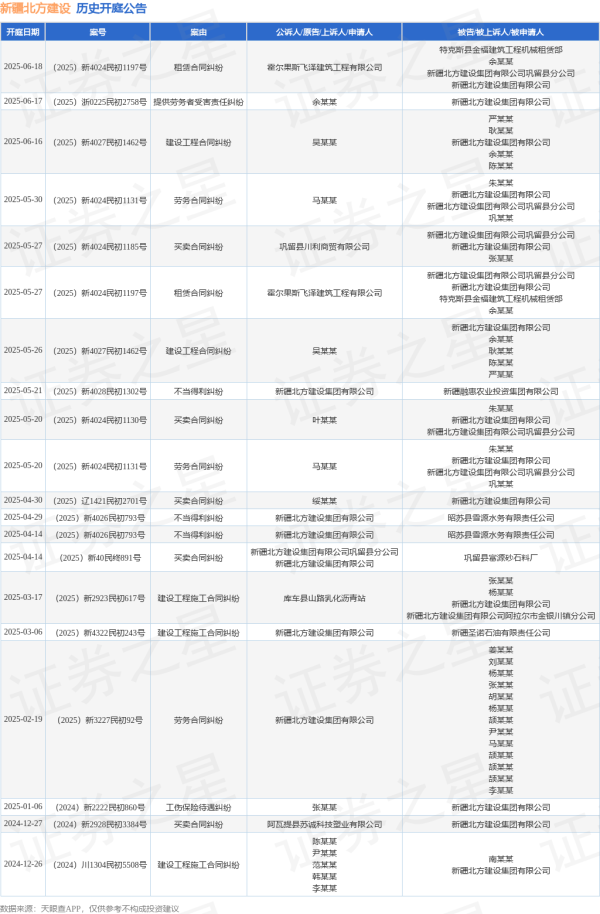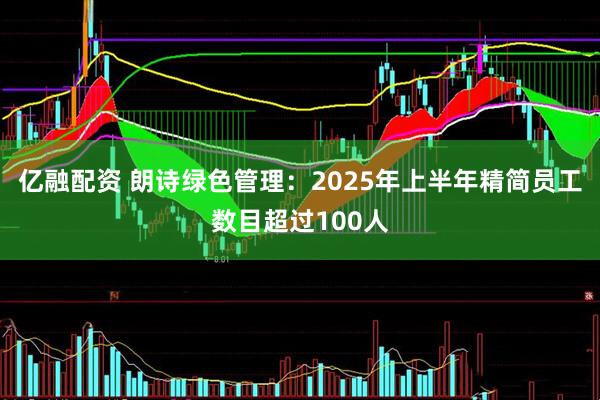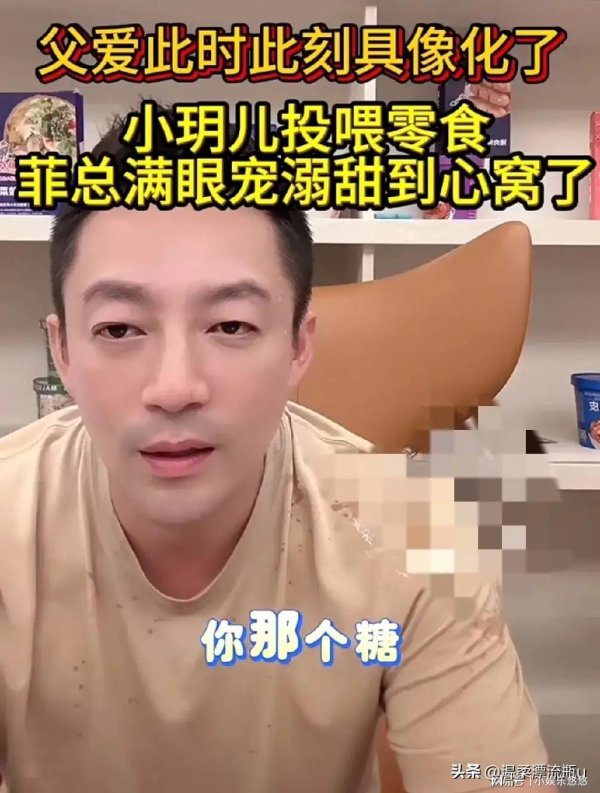京城危急,崇祯连发数道勤王诏令,盼各地将领火速进京护驾。左良玉手握重兵保宇配资,却始终按兵不动,任由大顺军破关入城、皇帝煤山自缢。
他是明末最后的王牌,却没迈出那关键一步。
从寒门武夫到封疆悍将
左良玉出身寒微,家在山东临清。早年父母双亡,由叔父带大。他天生臂力惊人,习武勤练,擅长骑射。年纪轻轻就投军辽东,在边镇营伍中摸爬滚打。最初只是个普通兵卒,靠在战场上拼命积累功劳。他不识字,但思路清晰,打仗狠,做人不服软,下属怕他,百姓怵他,朝廷却不得不依靠他。
初在辽阳镇任车右营都司,调入昌平军,后又从曹文诏征战山西。前线吃紧时,他常被调去堵口子,从松山打到杏山,每一战都不是轻松仗。他从没接受过系统军官训练,但每次都打得敌人掉头就跑。部队纪律差,军饷不到,民愤大,他依旧压得住。士兵听他的,不是因为尊敬,而是因为知道他要人命快,不打仗死得更快。
展开剩余87%朝廷看中他能打,开始提拔他。总兵,挂节钺,封伯爵,送马,送甲,送钱。都送,不然他不走。他不忠君,也不反叛,就是谁给粮他听谁的。他带的“左家军”日渐成形,从河南打到山西,从山西压到湖北,每战过后,活下来的士兵就跟狗一样跟着他跑,因为只有他能让他们活命。
崇祯六年,他在涉县、辉县剿灭流寇,战绩突出,升任总兵。两年后又被调往河南,镇守豫西门户。大顺军、张献忠余部、流寇、地方绿林,各路势力全在这片区域出没。他的战法简单粗暴,一打就是全线推进,不管后路,不顾补给,冲进去先杀一阵再说。他几乎从不按兵法出招,但敌人总挡不住。
流寇一听是左良玉带兵,就改道。他也趁机收编一些地痞流氓当前锋,把正规兵力留在后面作支撑。谁敢乱动就砍脑袋,结果就是他治下军纪反而比别人强。这种狠人,朝廷既怕又用。
崇祯十一年,他参与镇压张献忠。兵力不及,局势复杂,但他打得极猛,虽没能彻底平乱,却立下不少战功。京城传诏封赏,加金银、赐封号。他收了奖赏,但始终没动过一念之忠,他是朝廷的兵,却不是崇祯的人。
这时候,他已成中南重镇武力支柱。河南、湖北一带无将能制他。他握兵、控饷、理政,手上十几万兵,号称二十万,含辎重、流兵、杂役,甚至还有乡勇、商团,全听他号令。江南税赋、运河漕运多受其掌控。他虽不受文官待见,却是明朝最后几位能打的武夫之一。
京师告急,皇命连下
崇祯十五年,李自成卷土重来。西北战线失守,潼关陷落,河南半壁不稳。大顺军连破郾城、汝阳、洛阳,兵锋直指开封。皇帝震怒,急调各路兵马北援开封。左良玉在名单之中。他原驻守武昌,是南线重镇。开封若失,中原门户洞开,南北断裂,崇祯急了,调他北上。
兵符下到手上,他犹豫了。军中缺粮,士兵连年征战,很多人鞋都没有。几十号粮秣官在襄阳被杀,漕运断绝,开封一线没人敢护粮车。他不是没打过这样的仗,但这次他怕打赢了也得不到补给。
朝廷承诺给银十万两,布三万匹,还许他儿子做副总兵。他接了,但心里没底。他知道北援是死局。四十万人援军集结在朱仙镇,实为乌合之众。指挥官丁启睿无战功,空降上任,只会纸上谈兵。他提议据守南线,与主力会合后再图攻守,被丁否决。
朱仙镇一役没开打就崩。夜半起风,营中起哄,几处火起,士兵以为敌至。丁启睿不敢出营,被活活吓瘫。左良玉看到大势已去,连夜拔营撤往襄阳。没人阻止,他带走了最完整的一支部队,丢下朱仙镇数十营溃兵。全军瓦解。
这之后他成了战犯也成了救命稻草。崇祯一边命廷杖丁启睿入狱,一边又发银五万赐左良玉,命其回武昌固守南线。朝廷嘴上责罚,手上照样送钱。他成了两难之中的唯一可用之人。
崇祯十七年,局势崩坏。李自成攻下太原、保定,渡过黄河,进逼北京。京城文武几尽崩溃。内阁一边筹款修缮城防,一边连发数道急诏,命各地将领勤王。左良玉再次被点名。他已镇守武昌两年,此刻军力号称恢复至十五万,但其实粮草未足,战马不全,伤兵多,兵籍名实不符,水分大得惊人。
他再次接诏,但仍未动。他向朝廷上表称,长江水涨,运输不便,北线饷道断绝,兵未整补,请缓动。他不敢动,一动就没回头路。一旦进军中原,武昌无人可守,地盘失了,家眷留在敌后,京师未必能保,自己先输到底。
他没动。京城没等来他的兵。崇祯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,城破时内无粮,外无援。援军全灭,勤王无果。他在武昌听到消息,冷眼不语。朝廷已无,皇命不再,他仍握重兵自处,进退由己。他后来投效南明,却始终以兵权为要,从不为谁卖命到底。
拥兵在手,却不北上
京城以外,李自成的攻势越来越近。崇祯十七年春,潼关、太原、汾州相继失守,京师危机已迫在眉睫。朝廷下诏“勤王”,勒令各路将领北上护驾。左良玉在武昌、湖北、河南一带握兵,被视为能在关键时刻救朝廷的一支重力量。
左良玉领命后,拟出“勤王方案”。他令部将统计粮草、审查兵马,设立调度路线,希望从江南经湖广、河南北上。部中将领、壮丁数万人合围一带,又有地方募兵加入。他拟定沿长江运粮道通过荆州、襄阳等地,集中兵力后往南直抵京师。这样的方案一旦成行,可以在敌前形成一股制衡力量。
可军心未动。部队中多是流兵败卒、乡勇杂役。士兵抱怨饷银拖欠、衣被破旧、行军劳苦。粮道被水阻、漕运不顺。地方百姓逃乱,补给仓库被抢,或者税粮没赶来。左良玉下令筹粮,却被湖广地方官僚推诿,漕运桨声弱,粮船难进。几次试图出发,都因供给断绝、伤病、流寇骚扰而被迫暂停。
朝廷在北京多次发出急诏,责问左良玉:“护驾命在旦夕,何尚迟疑?”左良玉上疏,陈述局限,希望朝廷解除后顾之忧。然而朝廷重赏封号、许诺增补饷银,却仍难以克服实地补给困难与部队士气滑落。他哭于兵帐之中,自叹若不进忠心被误解,也无法推进军务。
兵力之名,支持之实远不足。左良玉手下虽号称数十万,但其中流寇降卒比例极高。训练混乱;装备差异大;将领指挥不一。敌人的战鼓、号角声中,往往最先散的不是敌军,是这类拼凑起来的部队。
当京城形势更恶,李自成逼近,北京内外通道被围,朝廷再催勤王。左良玉内部氛围终于出现分歧。部将主张速进京赐护驾令;另有声音说暂守重镇、稳固江南更为要紧。左良玉并未强行指挥大军南下。他虽有意动,却无力统一部下意志与资源。
京城陷落前的一刻,命令尚未落实。诏令传到武昌,数日寂静。李自成军已破门,崇祯帝自缢。左良玉却还在江边,望不见朝廷的旗帜,听不到京城的重锤。他未能进京护驾。护王命令失去时效。
崇祯命尽不是因兵少
朝廷内部财政毎况愈下。连年战乱,国家银两散尽,户部、吏部、兵部皆感囊中羞涩。朝廷承诺对将领的银两、布匹、马匹补给,往往滞后或未能兑现。左良玉所需的粮草、军需物资、补给顺道依赖沿途官署与民户,但这些地方早已被战乱扰乱或压榨殆尽。补给线一断,军队停滞。
崇祯皇帝性格急躁,重责轻信。佳将有功则赏,稍有失误则苛责。朝中信任与猜忌交错。左良玉虽有功,却也被怀疑若成名太大会自立门户。崇祯怕将领拥兵自重,怕他们坐大。于是赠封、赐号,却不给他完全自主权力或委以护京重任。左良玉虽被封为宁南侯、被赐封号,仍承担边防与镇贼任务。
朝廷体系调度混乱。命令下达到武昌,需经多级奏折、巡抚催办、巡视官回奏,时间耗费,效率极低。左良玉若要动员、募兵、调粮、调马、调人,不是一纸诏令可完成。南北之间河道舟车阻塞;地方强压逃役、征粮不顺,种种阻力交错纠缠。
此外,朝廷已经失去控制很多地方。地方流寇、贼寇乱起。边疆将领各有主张。京师之外的将领常常恐惧敌寇绕后、自己的地盘被染指。若左良玉东北南北疾行,离开武昌、荆州、襄阳,背后防线一定空虚。他必须权衡:若进京也许救朝廷,但自己的部众与地盘便易被敌人撼动。
控制兵权者之间的信任缺失。崇祯未能提前建立有效中央对将领的统御体系。赏赐与惩处交替。封号有,但补给与权力未同步。左良玉在多次被命勤王后,得到封赏,却未见朝廷能实质改变他手中的后勤与资源状况。他的建议与请求被接受,却未被满足。
当命令真正到达武昌,李自成已声震洛阳、占据河南大部。京师警报四起,但外援迟到。左良玉动员仍在准备。护驾令通知,他还在审兵调补。
京城最后崩溃之日保宇配资,他未曾启程。朝廷已无力再调动大规模援军。崇祯自缢之时,左良玉的勤王方案成为空谈
发布于:山西省嘉正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